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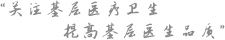
“事情是這樣的,今天上午,一位患者家屬打電話求助,說老人突然頭暈、惡心,讓我馬上過去,考慮到這個患者常年臥床不起,行動不便,我立即趕了過去,初步診斷爲眩暈症。我建議她到醫院做檢查,以便進行正規治療。可老人家屬一臉愁容地說:‘家裏實在沒錢去大醫院輸液了,你就在家給她輸液吧!’聽著老人家屬近乎哀求的話,我心一軟,就答應了。我觀察了十幾分鍾,確定沒有不良反應就回去了。1個多小時後,老人家屬來電話:‘大夫,她心慌、胸悶,快來看看吧!’我立即帶上聽診器、血壓計、急救針向老人家沖去。原來,在我走後,家屬調快了輸液速度。于是,我趕緊調整好滴速,一直等到輸液結束。”
面對患者的需求,我們到底應不應該出診?
無論你是社區醫生還是鄉村醫生,相信你也一定有過出診的經曆。面對出診,您是否也感到無奈和心驚膽戰?當前,一邊是居民的醫療需求,一邊是毫無政策和法律保障的醫療風險,我們如何才能做到兩全其美?
風險大但需求多,基層醫生出診很無奈
當前,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城市社區,老年人群中高血壓、冠心病、心腦血管的患者逐漸增多,特別是在農村,家庭中的年輕人多出去務工,家中僅剩下孤寡老人和兒童,爲滿足他們的醫療需求,作爲基層醫療機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村衛生室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出診任務。
2006年,衛生部印發《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管理辦法(試行)》,其中第7條規定:“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提供以下基本醫療服務,其中包括家庭出診、家庭護理、家庭病床等家庭醫療服務。”
但這條規定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第14條“醫師經注冊後,可以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按照注冊的執業地點、執業類別、執業範圍執業,從事相應的醫療、預防、保健業務”相沖突,醫生的出診行爲已經不屬于在注冊的執業地點行醫,嚴格意義上屬于超範圍行醫。
河南省新密市鄉村醫生付文娜介紹說,“我們的服務對象都是住在一個村、擡頭不見低頭見的鄉裏鄉親,他們有個頭疼腦熱或者不方便來衛生室就診的,就想讓我們出診,但是,對我們來說,風險太大了,我們的出診行爲是違反《執業醫師法》規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出事,我們就完全處于被動地位。特別是在農村,只要出事,醫生就要承擔全部責任。”
“出診過程中,不僅患者安全存在風險,醫務人員也面臨很大的人身威脅,比如有些居民家中養狗,但出診人員不知道,被狗咬傷。另外,出診任務中,護士比較多,都是女同志,如果居民家中僅有男同志,騷擾女護士的現象也是有可能發生的。”北京海澱區北蜂窩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院長張厲娜補充說。
“對于確實行動不便或病情不允許的患者,切實有出診需求的,我們也樂意出診爲他們服務,但是,我們經常還會遇到一些蠻不講理、胡攪蠻纏的患者。”村醫阿娜在其微博上表示,由于東北冬季天氣寒冷,經常有患者以天冷爲由,讓村醫上門爲其量體溫、送感冒藥,如果醫生婉言拒絕,患者還要惡語相向。
采訪中,我們發現,最讓基層醫生爲難的是,衛生行政部門這麽多年來一直沒有出台相關政策或規定,明確說明哪些情況下應該出診,哪些情況下不應該出診。
當前,在沒有政策指引,也沒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我們如何才能既能滿足居民需求,又能降低出診風險,保證醫療安全呢?
根據患者具體情況,選擇出與不出
面對居民的需求,醫生在出診時首先應對出診首先應做到心裏有數——什麽樣的情況可以出診,什麽樣的情況堅決不出診。開封市2010年全國優秀鄉村醫生何傳義曾表示,“我一般不給4種患者出診,即年齡太小的,年齡太大的,有嚴重慢性疾病的,說話盛氣淩人、帶有敵意的。遇到這幾類患者,我都建議他們去醫院治療,即使出診,在出診過程中我也堅決不會給患者在家中輸液。”
北京市大興區魏善莊衛生院社區科科長井利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社區醫療機構在出診時應該考慮一定的條件,如果患者爲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類等慢病患者,在社區醫療機構有過用藥史,且有家屬陪護,可以考慮出診,但是對于那些家中無家屬陪護,病情不穩定且首次診療的,一般不建議出診。
對此,張厲娜介紹說,“在我們轄區內,對于符合出診條件的老人,如病種簡單、病情穩定的患者,我們都會出診,出診內容和任務一般包括抽血、打針、輸液、導尿等等,如果輸液,我們嚴格遵守規定,對于一些容易發生意外的藥品,如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和抗菌藥物堅決不輸。”
“現在社區醫生上門服務的內容多以健康教育、婦幼保健、孕婦訪視等保健項目居多,一般不在居民家中開展診治行爲,在我們社區,上門輸液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爲社區醫生一般不能在輸液過程中隨時監護患者,萬一産生不良反應,普通居民家中又不具備醫療搶救設施,出現意外容易延誤病情。”成都高新區合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務科長程小川介紹說,建議所有的基層醫生出診時必須嚴格掌握適應證,確保醫療安全,對患者及家屬提出的不符合醫療安全的出診服務要求,醫護人員有權拒絕,但要耐心、友好地解釋原因,以取得患者的理解。
出診充滿風險。因此,醫護人員在出診過程中要提高安全意識,除了要求醫護人員務必攜帶搶救藥品和器械、嚴格遵守診療規範外,對于患者也要做好相應的醫療安全教育。以出診輸液爲例,無論是鄉村醫生還是社區醫生,在輸液過程中全程觀察患者是不可能的,因此,向患者及家屬告知輸液過程中的有關知識就顯得尤爲必要,如更換液體、拔針等注意事項,並囑咐在輸液過程中不可隨便調整輸液速度,一旦患者有異常情況應立即關掉輸液開關等等。
簽訂協議書,保護醫患雙方合法權益
基于當前出診對醫患來說都存在隱患,爲了最大程度地保護雙方,出診過程中需要進行操作類的護理和治療時,醫生應首先告知有關風險,並與患者或患者家屬簽訂知情同意書和協議書,以保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
“需要上門輸液者,必須在第一次出診前與患者簽訂家庭輸液協議書,由醫護人員詳細告知患者及家屬家庭輸液的注意事項、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所采取的應急措施。”張厲娜介紹說。
“需要提醒基層醫生的是,醫患雙方簽訂的知情同意書和協議書,僅僅是向患者告知有關意外風險有可能發生的一種書面文件證明,並不意味著在發生醫療意外時醫方可以免責,如果基層醫療機構人員在出診時,人員資質、執業資格及診療過程存在瑕疵,可以說,同意書的簽訂並不影響責任的劃分。”北京金棟律師事務所唐澤光介紹說。
雖然簽訂的協議書不是醫方的免責條款,但是協議在一定情況下仍然是有效的,這主要取決于醫方行爲是否符合診療規範,如果患者的損害後果與出診行爲並無關系,如患有冠心病的老年患者在輸液中突發心肌梗死,經鑒定,患者的死亡和輸液行爲並無關系,此種情況下,協議就是有效的,醫方就不需要承擔責任。
很多村醫與患者簽訂協議書時往往只寫上類似“患者同意輸液,一切不良後果由患者承擔”等字樣,殊不知,這並未體現醫生的告知義務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權,一旦出現意外,在法律上不可以作爲證據
呼籲給予法律和政策保障
對老百姓來說,醫生出診滿足了其醫療需求,拉近了醫患之間的距離,但是對基層醫療機構和基層醫生來說,出診卻沒有政策和法律保障。采訪中,多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院長呼籲能盡快出台政策,明確出診的細則和規定,但多省衛生廳的有關人員都表示,“醫生的出診行爲確實存在與《執業醫師法》的有關規定相沖突,但目前,我們也沒有見到上級部門出台政策或有關法規來進行調整和規範。”
记者手记 云南省福贡县拉马底村最美鄉村醫生邓前堆,28年溜索横跨怒江为两岸村民解除病痛。这样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虽然像邓医生这样身处如此恶劣环境的医生只是少数,但不论严寒酷暑随时去出诊的经历几乎每个基层医生都有过,我们在被他们感动的同时,也在为这一服务百姓、挽救生命的行为没有法律保障而感到痛心,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出诊行为以法律和政策支持,我想,这才是对其权益的最好保障。
評論




